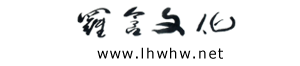哭罗木夫【五首并序】
明 罗洪先
十载江城面,三年夜雨亲。
道交久不厌,志逸老能贫。
岁月怜分影,乾坤隔幻身。
残躯新读礼,感事倍伤神。
彩服趋庭处,乌巾对月吟。
橙溪秋自好,椒醑尔难寻。
蝶梦无醒枕,猿哀有泪襟。
思亲悲似貌,今日失知音。
叔夜尘缘薄,初平道气深。
酒醒仍荷锸,身老不留金。
白日哀回驾,青鸾渺去音。
臯比读易事,凄断不堪寻。
阴阴伤岁暮,历历对山原。
呜咽泉声断,萧森桂影翻。
牛衣空自去,鹤树竟难言。
长岁归鸿急,荆丘日露繁。
招魂路杳隔,埋骨日幽阴。
岁月芳兰歇,风霜宿草深。
罗含留故宅,锺子絶鸣琴。
把剑悲重约,题碑寄夙心。
余壬辰秋九月,与三潭子泣别同江之渚。时先大夫在堂,而余之远行,实出公期促迫。期改岁当假王事南归省觐,与三潭子必重晤,得徜徉山中,与菽水乐。别未半朞,而先大夫见背;逾月,则三潭子亦相继摧逝。明夏奔归,则与三潭子永隔,而江渚之泣,盖永诀矣。哀哉!乙未倚庐将毕,追思故交,心肺割裂,遂抑郁宣悲,为挽诗八章。虽于声律之学或未谙识,至于论世,庶有征焉矣。
---
【解读】
罗木夫,名辂,字木夫,世为山原罗氏。祖时济,为宋吉州推官,明代学者罗洪先父亲挚友,亦为罗洪先老师。组诗融合了个人丧亲之痛与师长离世之悲,情感沉郁,意象苍凉。
一、主题与情感
1.生死之痛
"残躯新读礼"暗指作者守丧("读礼"即守丧期间研习丧仪),而"先大夫见背"(父亲去世)与师长"相继摧逝",双重打击下,"感事倍伤神"。
"招魂路杳隔,埋骨日幽阴"以幽冥意象,表达对逝者不可追的绝望。
2.知音之失
"今日失知音"直抒友人离世之恸,"锺子絶鸣琴"化用伯牙绝弦典故,喻知音难再得。
"江渚之泣,盖永诀矣"的序中追述,更强化了天人永隔的悲怆。
罗木夫为罗洪先之师,此组诗不仅是悼友,更蕴含尊师重道的深沉情感。
序中“先大夫见背”与“三潭子(罗木夫)摧逝”并提,罗洪先同时失去父亲(家学根源)与恩师(师门指引)。“罗含宅”既指罗木夫故居,亦可隐喻罗氏家学传统,二者叠加,形成“芳兰歇”“宿草深”的荒芜意象,喻示精神家园的双重崩塌。
二、“罗含宅”与“罗含菊”的双重象征
1.茅屋与兰菊:隐士风骨的投射
《晋书》载罗含“立茅屋”“布衣蔬食”,李商隐称“罗含宅里香”,皆以简朴生活与兰菊自生喻其超然物外。诗中“橙溪秋自好”“乌巾对月吟”暗合此典:
“橙溪”如罗含所居城西池洲,清幽避世;
“乌巾”(黑色头巾)为隐士常服,呼应罗含“晏如”之态。
罗木夫作为师长,其“茅屋”般的清贫与“兰菊”般的高洁,被罗洪先视为师道精神的具象化。
2.芳兰与宿草:德行与死亡的对照
原典中罗含致仕后“阶庭兰菊丛生”,象征德行感召天地;而罗洪先诗云“岁月芳兰歇,风霜宿草深”,却以兰菊凋零、荒草蔓延反写师逝后的精神荒芜:
“芳兰歇”暗指罗木夫之死如兰菊凋谢,德行随肉身湮灭;
“宿草深”(墓地经年之草)强化死亡对德行的吞噬,与晋书原典形成“生—死”“荣—枯”的残酷对照。
三、师道书写的隐逸化重构
1.“伐木为材”与“牛衣鹤树”的互文
罗含“伐木为材,织苇为席”,以自然之物构筑精神家园;诗中“牛衣空自去,鹤树竟难言”与之呼应:
“牛衣”(贫士粗衣)对应罗含的“布衣”,喻罗木夫安贫乐道;
“鹤树”(佛典中涅槃之树)升华师者之逝为超脱生死的精神飞升,暗含“白雀栖集堂宇”的祥瑞,却以“竟难言”道尽天人永隔之痛。
2.“菊香”与“泪襟”的情感张力
李商隐写罗含宅菊“香”赞其德馨长存,罗洪先却泣“猿哀有泪襟”:
“尔难寻”(“椒醑尔难寻”)直指师逝后,如罗含菊般的德行芬芳再难寻觅;
“泪襟”将李商隐的静态咏物转化为动态悲泣,凸显“德存而人逝”的永恒遗憾。
四、师道承续的绝望与希望
1.“招魂”与“泛菊”的仪式救赎
原典中兰菊因罗含德行自生,象征天道酬善;而罗洪先“招魂路杳隔”却质疑此道:
“招魂”是对“罗含菊”神话的解构——纵使德行感天,亦无法唤回亡魂;
末句“愿泛金鹦鹉,升君白玉堂”化用李商隐诗意,暗祈以菊香载师魂登仙,在想象中重构师道永续的可能。
2.“读易”与“题碑”的薪火隐喻
罗含“伐木为材”筑茅屋,罗洪先“臯比读易”“题碑寄夙心”,皆以文化符号重建精神栖居:
“读易”是承接师者学问的仪式,如罗含茅屋中的冥思;
“题碑”则是将师道刻入金石,对抗“宿草深”的荒芜,实现“兰菊”精神的文本永生。
结论:从“罗含神话”到“洪先之恸”
罗洪先通过解构“罗含宅里香”的德感神话,揭露了师道在死亡面前的脆弱性:兰菊可再开,而恩师不可复生;茅屋可重建,而问道之声永寂。诗中“芳兰歇”与“宿草深”的悖反,实为对儒家“三不朽”(立德、立功、立言)的深刻质疑——若德行不能超越死亡,“立”的意义何在?
然而,“题碑寄夙心”的终极书写,又暗示了文人最后的反抗:以诗为碑,将罗含菊的芬芳凝入文字,使师道在文本中“禁重露”“怯残阳”(李商隐句),完成从生命悲怆到文化永生的超越。